1949年,当李宗仁望着南京城被解放军攻破的那一刻,他的心情异常复杂。作为国民党的二号人物,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庞大政党走向溃败的根本原因。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话令人印象深刻:"军队为国捐躯,武器损失,弹药消耗自所难免,尚须行贿才可得到补充,实为千古未有的怪现象。"这句话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触目惊心的腐败内幕?为什么连最基本的军需补给都需要通过行贿才能获得?国民党的腐败到底严重到了什么程度?让我们跟随李宗仁的回忆,一起揭开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军需补给中的腐败链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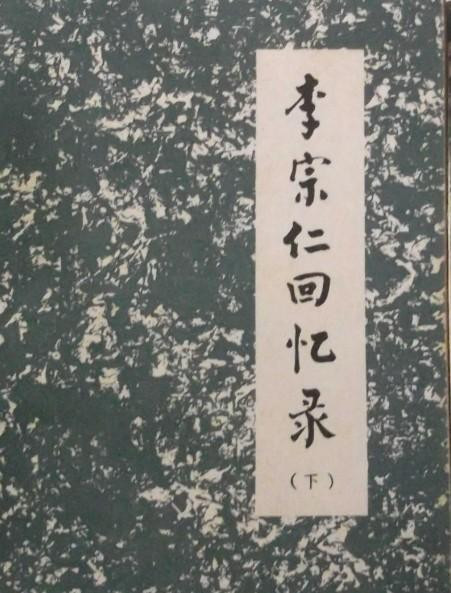
1947年冬,淮海战役正酣,王缵绪的29集团军在徐州一线苦战。当时部队弹药告罄,王缵绪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带着蒋介石亲笔批示的紧急军需调拨令,连夜赶到南京军需总库。
谁知军需总库的库长却连看都不看那份调拨令,只是冷冷地说:"现在物资紧缺,没有额外的费用,恐怕难以办理。"王缵绪一听就明白了,这是要收取好处费。但当时战事紧急,他只得咬牙答应支付"特别费用"。

转过年来,徐州战局更加吃紧。一位姓张的师长也带着调拨令来领取弹药,令人意外的是,他不到半天就搞定了补给问题。后来王缵绪打听才知道,原来这位师长早就和军需系统打好了关系,每次申领物资都会提前打点。

这种潜规则在军需系统中早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利益链。从最基层的库房管理员,到各级军需处长,再到军需署的高层,每个环节都要抽成。1948年初,傅作义的部队在张家口遭遇补给困难,他向军需署申请补充弹药。军需署派来的经办人直截了当地表示:"没有好处费,一颗子弹也别想拿到。"
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些军需官员甚至发明了"空单"制度。他们会开具虚假的领料单,把实际发放的物资数量少报,然后把多出来的部分倒卖到黑市。1948年夏天,在武汉军需分库就查获了一起大案,某军需官员利用这种手段,半年时间就倒卖了价值三百多万金圆券的军需物资。

到了1949年初,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在上海的一处军需仓库,管理人员甚至公然要求申领单位先交"手续费",否则连仓库的门都进不去。一位曾在军需系统工作过的人回忆说:"那时候军需仓库就像一个大型的私人买卖,谁给的好处多,谁就能拿到物资。"

即便是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危急时刻,这种腐败现象仍然存在。1949年4月,在南京撤退前夕,某军需仓库的库长居然还在盘算如何借机发一笔横财。他把库存的部分军需物资藏匿起来,打算等大部队撤退后私下倒卖。结果被解放军占领仓库时当场查获。
高层官员的贪腐之风

孔祥熙家族的奢靡生活在重庆时期达到顶峰。1941年,当日军的炮火威胁到香港时,蒋介石特意下令派飞机前往营救重要人士。其中一架军用运输机原本是安排接送包括胡政之、茅盾等文化界名流的,却被孔祥熙的二女儿孔令伟强行霸占。她不顾其他人的安危,带着十七条名贵宠物犬和一大群仆人登机。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她居然用手枪威胁已经登机的国民政府农村部部长陈济棠夫妇下机,只为给她的宠物犬腾出座位。

在重庆,宋家的排场更是让普通百姓望尘莫及。1943年,当大后方的普通民众还在为一日三餐发愁时,宋氏家族却在歌乐山上建起了豪华别墅。据当时负责采购的工作人员透露,光是宋美龄每周的生活用品清单就长达数页。从法国进口的香水、瑞士定制的手表,到意大利的高档皮鞋,无一不彰显着这个家族的特权地位。
军统特务在这种腐败风气的影响下,更是变本加厉。1944年,重庆某街区的一个水果摊贩因拒绝给军统特务免费供应水果,竟然被以"通敌嫌疑"为由关押了三个月。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甚至公开表示:"在我们眼里,不贪污受贿的反而最可疑。"

1945年抗战胜利后,接收敌伪产业成为了一些高官敛财的新途径。在上海,某高官的夫人以"考察"为名,带着一群亲信挨家挨户"视察"日本人留下的房产。短短三个月,就将数十处高档住宅据为己有。这些房产后来以低价转手给其亲信,再高价出售获取暴利。

即便是在1947年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期,这些权贵们仍然我行我素。当时重庆的一份普通公务员月薪还不够买一斤大米,而某高官的千金却在南京举办了一场奢华的生日宴会。据参加宴会的来宾回忆,光是餐桌上的法国红酒就价值数百万法币。
到了1948年,情况愈发严重。一位曾在国民政府工作的职员回忆,某些高官的亲属甚至把政府部门当成了自家的提款机。他们随意调用公款,采购奢侈品,甚至将公款直接转入私人账户。有位高官的公子在一年之内就挪用了相当于普通工人三百年收入的公款,用来在上海购置豪宅和古董。

就在国民党政权即将覆灭的前夕,这些权贵们仍不忘大肆敛财。1949年初,某高官家族趁着撤退之机,将数十箱黄金、古董和珠宝秘密运往香港。而此时,前线将士却连基本的军饷都领不到,只能靠发行毫无价值的金圆券来安抚军心。

政府机构的制度性腐败
1946年,国民政府军需采购处的一份内部档案意外流出,揭露了一个惊人的"回扣制度"。按照规定,凡是承接军需物资采购的商家,必须向采购处上缴30%的"手续费"。这笔费用层层分配:采购处长占10%,科长占8%,经办人占7%,剩下5%则作为"公共经费"。

在南京,一位姓陈的军需供应商道出了这个制度的具体运作方式。他透露,每次投标前都要先向采购处打点,否则根本拿不到订单。即便中标后,还要按规定比例上缴回扣。为了弥补这些额外支出,供应商们往往会以次充好,以劣充优。结果就是前线将士收到的军需物资质量低劣,有时甚至完全不合格。
1947年春,接收大员的"五子登科"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所谓"五子登科",指的是接收敌伪产业时的五种敛财手段:勒索、侵吞、中饱、克扣、贪污。某接收委员会的成员在接收一家日资纺织厂时,竟然要求原厂方先交纳100万元"接收费"。更荒唐的是,这笔钱连收据都没有,直接进了接收人员的私囊。
"白条党"的猖獗则是另一种制度性腐败的体现。1947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各部门开始大量发放白条,以应付各种支出。这些白条本应及时兑现,但往往拖延数月甚至一年都无法兑付。于是,一些官员和投机商人开始低价收购白条,再通过关系网络全额兑现,从中渔利。在南京,就出现了专门经营白条生意的"白条市场"。
到了1948年,这种制度性腐败已经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在广州某政府部门,一位基层职员揭露说,从门卫到处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费标准"。办事群众必须按照这个"价目表"逐级打点,否则连大门都进不去。即便是最简单的盖章手续,也要经过三四道"关卡",每道关卡都要交钱。
1948年底,重庆某税务机关爆出了一起大案。几名税务官员串通一气,专门找有钱的商家"合作"。他们按正常税额的一半收取现金,然后开具全额发票。这样既能让商家省钱,自己也能从中获利。据查,仅半年时间,这个团伙就侵吞了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千年工资的税款。
1949年初,当解放军已经逼近南京时,一些政府部门仍在进行最后的疯狂敛财。某部门的负责人甚至公开叫嚣:"再不捞就没机会了!"于是,各种审批手续的"加急费"猛涨十倍,一份普通的证明文件也要收取天价费用。有的官员干脆把办公室搬到了自己家里,明目张胆地收取各种名目的费用。
这种制度性腐败最终演变成一种独特的官场文化。在某些部门,清廉的官员反而会受到排挤和孤立。有位老职员回忆说:"那时候,不贪的反而像个异类,大家都觉得你不合群。"一些年轻的公务员为了在机关立足,不得不学着"入乡随俗",逐渐适应这种潜规则。
基层官员的鱼肉百姓
1946年秋,江苏省某县的征粮风波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县长王某为完成上级下达的征粮任务,不但强征农民的口粮,还派出警察挨家挨户搜查。一位姓张的农民因藏粮被发现,竟被当场吊打。更令人发指的是,县府的征粮队不但抢走了他家仅存的粮食,还抢走了用来支付子女学费的积蓄。
在浙江某乡,一位乡长利用职权之便,将救济粮变成了敛财工具。1947年春荒时节,上级发放的救济粮本应免费发放给贫困农民,但这位乡长却把救济粮高价卖给粮商,然后只给农民发放少量霉变的陈粮。当地一位老农回忆说:"那时候,就连救命的粮食也成了他们发财的工具。"
1947年底,四川某县的税务所长搞起了"税收承包"。他将各乡镇的税收任务层层发包给地方恶霸,这些人可以随意加收税款,只要按时上缴规定数额即可。结果就是,一些地方的实际税负比正常标准高出三到五倍。有的农民交完税后,连春耕的本钱都没有了。
山东某县的县府大门口,每天都挤满了来上访的农民。1948年春,当地一位姓刘的区长勾结地痞,以"剿匪"为名,大肆敲诈勒索。但凡家境稍好的农户,都被扣上"通匪"的罪名,必须交钱才能平安。据统计,仅三个月时间,这个区就有超过二百户农民被迫典当田产、卖儿鬻女。
在广东,一些基层政府甚至把罚款变成了创收手段。1948年夏,某镇公所规定,凡是在街上吐痰、随地大小便者,一律罚款五万元。这个数字相当于普通农民半年的收入。更荒谬的是,执法人员专门躲在角落里"守株待兔",见人就罚。当地百姓无奈地说:"现在出门连口水都不敢吐。"
湖北某县的县政府在1948年下半年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协助费"。任何人到政府办事,除了正常规费外,还要交纳数额不等的"协助费"。这笔钱的去向成谜,没有收据,也没有账目。一位老商人回忆说:"那时候去县府办事,口袋里没带够钱,连门都进不去。"
到了1949年初,一些地方的基层政权已经完全蜕变成了敲诈勒索的工具。安徽某县的一位区长甚至把"摊派"制度化,每月都要向辖区内的农户收取各种名目的费用。从"治安费"到"卫生费",从"文化费"到"建设费",名目之多,令人眼花缭乱。农民们苦不堪言,但敢怒不敢言。
在江西某县,一位粮站主任巧立名目,克扣农民卖粮款。他规定,所有收购的粮食都要扣除"水分"、"杂质"等,实际扣除的比例却远超标准。被克扣的粮款自然落入了他的腰包。当地农民编了一句顺口溜:"十斤粮食九斤水,收了粮食不给钱,农民伸冤无处告,眼泪只能往肚咽。"
金元外逃与资产转移
1948年下半年,随着战局的急剧恶化,各地掀起了一股疯狂的外逃潮。上海的金融市场首当其冲,某银行的经理在一个月内就秘密抽调了相当于普通职员三百年工资的资金,通过地下钱庄转移到香港。这些资金在转移过程中,又被层层盘剥,最终到港的金额还不到原数的一半。
南京的权贵们则选择了更为隐蔽的方式。1948年10月,某高官的夫人以"采购医疗设备"为名,携带大量黄金经香港转道美国。据当时浦口海关的一位老关员透露,光是这一趟就转移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黄金。为了掩人耳目,这些黄金被做成各种首饰和工艺品。
在广州,一些官员选择了更为迂回的路线。1949年初,某省政府官员以"考察农业"为名,带着一批"调研人员"前往台湾。这些所谓的调研人员,实际上都是搬运工。他们分批将大量的古董字画、珠宝玉器运往台湾,再转运国外。据统计,仅这一个团队就转移了超过三千件珍贵文物。
重庆的外逃方式则显得更为粗暴。1949年2月,某军需仓库的负责人直接动用军用运输机,将仓库中的物资运往香港。这些物资本应用于军队补给,却被他们以极低的价格抛售。一位当时在香港的商人回忆说:"那段时间,香港的市场上到处都是这些贱卖的军需物资。"
天津的金融界也未能幸免。1949年初,某银行的高层主管利用职务之便,将大量存款转为外汇,然后通过各种渠道转移到海外。他们甚至不惜以超过市价三倍的价格收购美元,导致天津的外汇市场一度陷入混乱。当地的小银行纷纷倒闭,而储户的存款却早已被转移一空。
在上海,一些精明的商人选择了更为隐蔽的方式。他们将资产转化为各种贵重物品,如钻石、名表等,然后通过"水客"偷运出境。1949年3月,仅一个星期就有价值超过百万美元的钻石通过这种方式流向香港。这些钻石后来又被转卖到欧美,最终成为这些人在国外的第一桶金。
武汉的某些官员则把目光投向了国际贸易。1949年初,他们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了大量的生丝、茶叶等出口物资,然后通过香港的中间商高价卖给国外买家。这些交易的差价直接进入他们在国外的账户。据不完全统计,仅此一项就造成国家外汇损失数百万美元。
最后的疯狂出现在1949年5月前后。当解放军已经进入长江流域时,南京某机关的负责人居然还在组织"经济考察团"。这个所谓的考察团携带了大量的公款和贵重物品,以考察为名,分批撤往香港。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去了美国、加拿大等地,利用这些转移的资产在当地开设公司、购置房产。